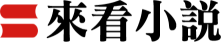第三十七章 求饒
晚飯後周家老兩口躺在牀上,周有成早睡早起腦袋裡不想事,沾枕頭就睡了。
鄧紅梅睡不着覺,戳了戳周有成,“別睡這麼早,起來說幾句話。”
“說……說什麼?”
鄧紅梅嘆了一口氣,“我聽說雄慶和他老婆打算在市里買房子。”
夜色靜得出奇,周有成嗯了一聲,沒有音。
“我跟你說話呢。”
在老頭身上掐了一下,“啊呀,啊呀!疼……”
“南川手裡也不是沒錢,讓他也去市里買個房子,省得雄慶他媽天天在村里嘚瑟。”
“你跟人家比什麼?”
“不是我跟她比,是她跟我比……說她兒子比咱兒子文化好,現在又在外企當高管,媳婦也是城裡人,樣樣都想搶咱們一頭!”
鄧紅梅沒讀書過,也沒什麼心眼,人家對她好,她自然而然也對人家好,偶爾發脾氣,但也講道理,眼瞅着佟言現在不作不鬧願意和自家兒子好好過,嘴上沒說,但心裡卻樂着。
然而總有人愛把之前的事揪出來說笑,她心裡不舒服,再加上日子跟着平淡下來,她不想兒子媳婦比別人家差。
“我當年嫁給你的時候蔣彩雲就到處說我沒文化,說你是聾子,我沒讀過書就是瞎子,說我跟你聾子配瞎子天生一對……”
鄧紅梅聽他沒動靜,打了他一下,“我跟你說話,睡什麼睡?”
“這點小事現在還記着,女人家小肚雞腸的。”
“這還小事?周有成,這叫小事啊?”
“別拽我,我困得很……”
周有成很快又睡了,鄧紅梅不依不饒,“我告訴你,就得讓她知道,我們家不是好欺負的,不是任由他們家踩在腳底下一輩子……”
“雪琪跟東亭處對象的時候你知道她說什麼嗎,說我們沒把女兒教好十來歲就嫁人生孩子,還說雪琪命不好,連生三個女兒,說這種生法克夫,傳到顧家那邊去了。”
她擦了擦眼淚,“酒席上你沒看見吶,那是故意跟咱們家比,樣樣都要搶一頭,雄慶再能幹又能怎麼地?還不是給人家打工的,能比得過咱們家南川?南川自己就是老闆。”
鄧紅梅喋喋不休,周有成睡得打鼾,她更氣了,一邊說一邊氣。
樓上,佟言有點渴,周南川下樓去打水,他腳步聲重,怕吵到兩位老人,故意放輕了些,走到門口聽到鄧紅梅的聲音。
“我跟你說話你當耳邊風?”
屋門正關着,周南川有些恍惚。
“一天到晚的,什麼也不關心,要抱孫子的人了還是什麼都不關心,這個家就我一個人累死累活,操不完的心!”
周南川拎了水壺往裡倒熱水,輕輕放下,端着杯子準備走,“我不管,我明早就說,讓南川在城裡買個房子,買個大房子,他們家雄慶打算在市里買,我們就直接買了,買個大的……我看蔣彩雲還拿什麼嘚瑟。”
二樓,佟言穿着睡衣坐在牀邊上,微微彎腰。
“怎麼了?”
周南川將水放下,“躺着,別着涼了。”
“有空調,不冷。”
“怎麼了,不舒服?”
佟言低着頭看他,心裡說不出的滋味,眼淚在眼眶裡打轉。
女人的眼淚說來就快,快得離譜。
“你又怎麼了?”
佟言揉了揉鼻子,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她對自己的評價很中肯,算不上多能幹的一個人,但也絕對不軟弱,她以前不太看得起動不動就哭的女人,覺得無法理解。
現在自己卻變成了這種人。
周南川要給她擦眼淚,她將臉別開,這下男人有點慌了。
“到底怎麼了,我惹你了?”
她搖頭,不說話,只是哭。
周南川抓着她的手,回想從園子裡回家後發生的一切。
沒發生什麼特殊的事,兩人邁着小碎步回家,路上遇到野狗朝他們叫,他撿起石頭把野狗轟跑了,她沒被嚇到,當時還一臉笑容。
回家後父母對她不錯,噓寒問暖,夾菜盛湯,飯後就回到了樓上,他絞盡腦汁想不明白能讓她哭的點在哪裡。
他蹲在她面前,有些無奈,“佟言,你有什麼話告訴我,別讓我猜。”
“周南川……”
她抱着他的頭,“我好害怕啊。”
“怕什麼?”
“生孩子疼,我怕,我不想生,我能不能不生了,我不想生孩子。”
聞聲,男人的臉瞬間沉了下來,佟言還抱着他,熱淚落在他臉上,一滴又一滴。
這些日子以來,她不哭不鬧,好好吃飯,好好睡覺,給他一種腳踏實地過日子的錯覺,給他買衣服,買襪子,甚至還願意配合他做親近的事。
在今晚之前,周南川覺得這就是他以後的生活了,人心是肉長的,不可能捂不化。
“周南川,我真的不想生孩子,我怕疼,我今年才二十歲,責任太大,我負擔不起……”
男人將她的手拿開,“你這段時間一直都想跟我說這個?”
她抽噎着,紅着眼睛。
“喝水。”他將杯子遞給她。
佟言沒接,周南川將她的手抓過來,讓她握着杯子,“周南川,我……”
男人沒在搭理她,靜靜的掀開被子在她身邊躺下。
燈關了,佟言窩在被子裡哭了一會兒,男人一動不動,完全當她不存在。
想發泄情緒卻又無人搭理,佟言受不了,從被子裡碰了碰他的胳膊,“周南川……”
男人喘着粗氣,氣氛再次陷入安靜。
她壓着哭腔,將頭靠過去,眼淚落在他肩上,“周南川……嗚嗚……”
周南川完全不想搭理她,只要他一回想起這些日子以來的溫馨生活都是她在爲不要這個孩子做鋪墊,他就覺得自己被當猴耍了。
他的真心被她踐踏在腳下,這個女人根本沒把他當回事,就算是他的人了,懷了他的孩子,依然策劃着離開這裡,逃之夭夭。
她的心是鐵做的?
眼淚吧嗒吧嗒掉在他衣袖上,佟言下意識抓着他的胳膊,越哭越傷心。
她的眼睛在他胳膊上蹭了蹭,“周南川……”
男人的防線坍塌了——
她才多大,二十歲,嫁給他本就突然,新婚那晚他又那樣迫切刺激了她,沒能及時適應自己的身份,人之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