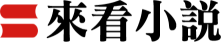段承瑞見過溫婉良淑的女子,也見過肆意大膽的女子。
卻未曾見過顧茗煙這般性格怪異的女子,他幾乎是眼睜睜的看着她那一雙巧手從溪水裡撈了兩條小魚上來。
“會烤魚嗎?”她大膽的將兩隻魚都扔上了大石頭,又手腳並用的爬了上去,揉了揉有些發癢的鼻尖。
“會。”段承瑞鬼使神差的回答。
之後,等他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和她坐在了篝火旁,兩隻小魚也都被她隨身帶着兩把小刀給整理乾淨,套在了兩根長長的木枝上,烤着。
她順帶着將身上溼漉漉的衣服給烘乾,臉上還帶着笑意:“我早就想試試自己捉魚,自己烤魚了,不知道味道怎麼樣……”
“你夜晚來到這圍場的林間,就爲了玩水烤魚?”段承瑞依舊不可置信的看着她,今日白日見到她身着一身樸素衣服,差點就認爲她是哪家不成體統的小姐,後來在高台之上才發現她就是靖王妃。
而如今,靖王妃搖身一變,成了捉魚丫頭,好生奇怪!
“還爲了騎馬,在天炎城裡我便想着要閱覽醫書,可一來到這荒郊野外,就想做些放飛自我的事情,而且,這不是還挺有趣的嗎?”顧茗煙俏皮的對他眨了眨眼睛。
世上做事哪裡需要那麼多的理由,大多都是想做便去做罷了。
“的確有趣。”段承瑞也跟着揚起嘴角來。
“不過你深夜來此究竟是爲了什麼?是想調查四皇子的事情,還是想要來毀屍滅跡?”顧茗煙話鋒一轉,眼神也冷了下來。
她雖然貪玩,卻也不是個傻子。
段承瑞只是笑着看她:“沒想到你一副單純模樣是裝出來的?”
“我可不是傻子,方才出了那些事情,有些地位的人自然都想將自己摘出去,你還在這樣進退兩年的情況下深夜前來,自然是有懷疑的。”顧茗煙搓了搓自己的手。
段承瑞的眼神一暗,卻是無奈道:“只可惜王妃多慮了,我來到此處,是想找到蛛絲馬跡,鈺兒是我四弟,我和他年紀相仿,自幼一起長大,我沒有母親和母妃,到總是他的母妃賢妃多照顧我,我斷不能看着有人害他。”
“原來如此。”顧茗煙眼神複雜,她對皇宮之中這些人的關係都了解的並不多,但看段承瑞這副模樣倒也沒有說謊。
若他真的是來毀屍滅跡,就不該在看見她之後還貿貿然的出來,應該躲着。
除非,他真的藝高人膽大,毀屍滅跡了之後還敢到她面前來。
但是這些跟她都沒有關係,而段承瑞將兩條魚給拿了起來,遞給了她一條:“熟了。”
“哦。”顧茗煙將烤魚接過來,瞥了一眼段承瑞,見他還是神態自如的模樣,也放下了戒心,只是這魚沒有調料果然不好吃。
吃完烤魚,她的衣服也幹了大半。
“時候不早,我還是先回去了。”顧茗煙騎上小紅,溜溜達達的往回走。
段承瑞對她點點頭,也竄入了林間,似乎是從剛才過來的地方返回。
段承瑞一路回到了自己的小院之中,房間裡卻早已站着一名高挑女子,她身着淺紫的衣衫,一見到段承瑞便站起身來,如果仔細看,便能看見她的腳邊還有一些泥土。
“事情完成的如何?”段承瑞斂去了方才溫和模樣,嚴肅的坐在了桌子的另一邊。
女子走到他的身邊爲她添茶,低聲道:“已經解決了,應當是無人能懷疑到您的頭上,而且,那處我已經留下了痕跡,四皇子的人去了也只會認爲是靖王所爲。”
“那就好。”段承瑞認真的點點頭,從口袋裡取出一包藥粉,扔進了火盆之中,燒毀殆盡。
“只是四皇子,妾身有一事不明,那靖王妃是如何發現四皇子餘毒未消,我們已經做的十分隱蔽了才是。而且,方才若不是您將靖王妃牽制住,我們怕是會暴露。”女子頓時皺起眉頭來。
段承瑞卻輕輕的揚起了嘴角,似乎是覺得這件事情十分有趣,卻並未多言。
女子以爲再得不到回答,便行禮離開。
屋內的燭火滅了,段承瑞卻不禁想起今日月色之下的那抹鵝黃色,和那淺淡的笑意。
這個靖王妃,當真是有趣的很!
另一邊,顧茗煙回到帳篷里,正看見段承鈺正將什麼東西藏到了背後,她不免疑惑:“在藏什麼?”
“沒什麼,只是王妃這麼晚了怎麼還過來?”段承鈺乾笑了幾聲。
“叫我煙兒就好,這麼晚,我就是過來看看你傷口還疼不疼,等會兒便回去睡了。”顧茗煙走上前來給他把脈,見他氣息不穩,眯着眼睛看他:“你是不是趁我不在吃了什麼火氣大的東西,雖說你是習武之身,但病了就要遵循醫囑知道嗎?明早我讓銀翹給你拿飯來,不許吃其他的了。”
“知道了。”段承鈺點點頭,看着她微微出神。
顧茗煙將草藥往他的枕頭裡塞了一些,這才離開,回到那小小的院落之中,而主屋門口,錦繡正蜷縮在那,她便瞭然,段承軒和蘇玉婉肯定睡在主屋了。
她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小屋裡洗漱了一番,沉沉睡去。
一夜安眠,可在這獵場衆人之中,卻是暗潮湧動。
三日過去,段承鈺已經好了不少,顧茗煙卻囑咐他儘量不要動自己的腿,臨走之時,段承軒倒是找到了皇帝,開口:“皇上,鈺兒受傷,在京城之中的府邸暫時無人,不如先到我的府上暫住幾日。”
“好,就這麼辦吧。”皇帝自然點頭答應。
段承鈺聽聞,臉色有些怪異。
“不如就讓他跟我一輛馬車吧。”顧茗煙直接接過了段承鈺,總覺得段承鈺今日狀態不佳,她等會正好給他診脈。
段承軒沒有阻攔,蘇玉婉則是巴巴的看着段承鈺和顧茗煙上了一輛馬車,她更想和這位皇子搞好關係,也好培養自己的勢力。
坐在馬車之上,段承鈺的臉色卻好了一些,而顧茗煙給他把脈,並無大礙,擔憂:“你究竟是怎麼了?”
“無事,那個,我可以叫你煙兒嗎?可以相信你嗎?”段承鈺突然擔憂的看了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