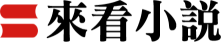季承煜把被子放到床上,别扭的说道,“这里是我的房间,你是我夫人,我为什么要去其他地方。”
方舒瑶觉得他像个孩童一般,幼稚却可爱。
这一夜,季承煜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想着这两日的一切,又想着他自己的种种反应脸色又暗了几分。
他莫不是真的喜欢上这个臭丫头了?想到这个,立马摇摇头,不会的,臭丫头除了长得好看一点,脾气又大,又野蛮,动不动还打人,这样的女人他才看不上呢。
第二日又是一个阳光和煦的清晨,季承煜打完拳来到前厅,一进去就听到里面传来几声笑意,还有浅浅的聊天声,眼神微眯,随后大步走了进去。
“季公子来了,舒瑶同我说你每日都要练武,不知道你的武功师承那家?”
“不过一些强身健体的招式而已。游公子见笑了。”走到方舒瑶跟前坐下,拉过她的手关切的问道,“夫人,你的身子可有好点?”
“已经好多了……”不经意间,见他胳膊处划破了一道伤口,紧张的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弄伤的?”
“刚才打拳的时候不小心弄伤的,无碍,夫人不必担心。”季承煜拉着她的手给了她一个安心的眼神。
游京墨坐在一旁,将季承煜的小心思全都瞧在眼里,随后不屑的笑笑。
用完早饭,季承煜拉着方舒瑶准备去书房,游京墨突然说道,“我听舒瑶说,季公子棋艺了得,不知道季公子愿不愿意与在下对弈一盘。”
游京墨如此聪明,季承煜不相信他不知道昨日的事情。可若既然知道,今日却还这般状若无事的样子邀请他一块对弈,那这人的城府,心计可就太深了。
原本不想去的,但是哪有防贼千日的道理。思量想去,点头应下。
一刻钟后,凉亭内。两人面对面坐着,桌上摆着一副棋盘,黑子已经走了一步。季承煜手持的白字却迟迟不落子。游京墨装作没有瞧见一般,悠然自在的欣赏着院子里的风景。
季承煜上活了两世可以说阅人无数,却第一次碰上游京墨这样城府如此深之人。刚才他观察了他许久却什么都没有看出来。
他到底是什么来历,医术精湛,心思深沉,这样的人真的会是一个无家可归之人?估计也只有方舒瑶那个傻丫头会相信吧。
“季兄可是有话说,在下洗耳恭听。”
心思被戳穿,季承煜没有一丝慌乱,把玩着棋子轻笑道,“游兄这般聪慧,又有一身本领,怎么会落到无家可归之地?”
“该说的在下之前都已经同舒瑶说过了,既然季兄如此关心在下,在下再说一次也无妨。在下初来驾到,又丢了钱财,一时落魄让季兄见笑了。”
“是吗?”季承煜似笑非笑的盯着他,“这样的说辞怕是只有我家夫人那样心思单纯的人才会相信。”低头看向棋盘,思量之后说道,“我瞧游兄气度不凡,执子熟练,应该是为高手,今日我们赌一局如何?”
游京墨仔细盯了季承煜一会,随后笑笑,“季兄打算拿什么做赌注。”
“你”季承煜说完看向他,“我们一局定输赢,如果游兄赢了,游兄可以继续住在方家,相反,如果游兄输了……,还请游兄自己找个理由立刻离开方家。”
游京墨似乎早就猜到他会提出这般要求,抬头看了一眼刺眼的太阳笑道,“在下不过一个无关紧要之人,季兄这般不欢迎在下,究竟为何?”
“游兄是聪明人,其中缘由还需要我一一解释吗?”拿起棋子,放到棋盘上,游京墨见状,笑着与他对弈起来。高手对决简直就是神仙打架,一局棋下了两个时辰还没有分出胜负。季承煜越发觉得这个游京墨心思深沉了。
他的棋艺是当特种兵的时候学的,教官说这个东西最考验耐力,起初他极为不适,慢慢才找到其中的乐趣,平日里一没事就和队友对弈,十几年来,几乎没有遇到过对手。只是今日……
“季兄,承让了。”游京墨放下最后一颗子,笑着站起身。
愿赌服输,季承煜认了。“你放心我说话算话,不过,若是让我知道你打着什么坏主意,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起身离开了凉亭。
游京墨站在凉亭内盯着他的背影,心思微转,这个季承煜到底是什么来历,不过一介书生,竟然有这样的气魄与心思,以前他怕是小瞧他了。
书房内,季承煜坐在桌案前一刻钟不到,叹了十几次气,书上的字却一个都没有看进去。方舒瑶见状,合上账本问道,“你怎么了,不是与游京墨下棋去了吗?”
“别跟小爷提他,道貌岸然的家伙。”冷哼一声,拿过游记假装看书。
“你又发哪门子的疯啊。”方舒瑶一脸莫名其妙,“你这两日这般反常,真的与游京墨无关?”
“他与我何干,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我先出去了。”季承煜心虚的起身出了书房。方舒瑶瞧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不厚道的笑笑。
这个臭男人,心思都这么明显了,她又不傻,怎么会瞧不出来。
临近午时,方舒瑶出来透气时,遇上了游京墨,想到上午季承煜的反常,笑着走上前,“上午对弈,我家夫君是不是输的很惨?”
来方家也有几日了,关于方舒瑶和季承煜的婚事他也听了不少,原本以为这般匆忙成婚的两人关系一定不太好,但是这几日瞧下来,他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如今又听到她这般自然,亲昵的称呼季承煜,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
“季兄是个很好的对手,与他对弈,我是受益匪浅。”
“你啊就别拿这些客套话敷衍我了,快同我说说,他是不是输了?”方舒瑶总觉得季承煜刚才莫名其妙的发脾气一定与这件事情有关。
游京墨见她这般想知道,思量之后,点头回道,“是,不过半子之差,我不过是侥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