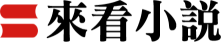挂了电话,陶陌把玩着手机,眼里闪烁着危险的暗光,那些上不了台面的黑恶手段掠过心头,每个都是烂熟于心具有可操作性和百试不爽的有效。
但是,他要用这种阴司手段来对付祁阳——对付一个他亲口说了喜欢的人吗?
陶陌深吸一口气,压下越燃越烈的狠辣念头,他要得到这个人,但绝不是要毁了他。临走之前,祁阳失望和抗拒的眼神便让他痛如刀绞,他不能想象,如果祁阳真的恨起他来,他该是如何的难以忍受。
所以这次的安排决不能不折手段,毕竟此意不在对付往常那些水火不容的商业对手,而是要挽回他喜欢的人。
……喜欢的人。
陶陌神色微微怔忡,口中喃喃把这四个字又咀嚼了一遍,那缠绵在唇齿间的酸甜滋味,让他禁不住露出了一个不带任何与他相匹配的形容词,反而称得上柔软的笑来。
“祁阳……”分别如此短暂,他的思念却已经不堪忍受,那个人在做什么呢,也在像自己思念他一样在想着自己吗?
“叮铃铃——”祁阳猛的抬头,这才发觉,不知何时窗外已经天色近晚,屋里昏沉沉,只剩最后几许落日余晖的光了。
面前茶几上摆着端正的诊断书,烟灰缸里掐灭的烟头铺满一层。
他维持这个坐姿已经很久了,伸出手去拿手机的时候,肩膀酸痛的犹如坠了大石。
屏幕亮着光,手机铃声还在顽强的响着。
在看清楚来电备注之后,祁阳的瞳孔骤然一缩。
陶陌两个字像是无形的刀尖,深深戳进他疲惫的视野里。
理智上清楚他需要宁城的工作,不然别说那遥遥无期的二十万,光是维持生计都将是问题,可在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后,他又该如何与陶陌相处?
千头万绪只在电光火石间一晃而过,他沉默的时间许久,总觉得铃声在下一秒便会自己挂断,让他可以不陷入这样的两难。
但是没有。
这个来电就像那个混账东西一样咄咄逼人,持续不停的响着铃儿,似乎要和他对峙到底。
祁阳抿了抿嘴,神色冷淡。
他不可以意气用事,哪怕是为了祁明,也不能光凭好恶来行事,上次贸然辞职,差点便让家里断了经济来源。这次……
祁阳缓缓放松了紧绷的肩膀,点下了接通。
沉默。
寂静的室内,只能听到两道呼吸声在彼此交缠着。
似乎亲昵,又感觉尴尬,祁阳几乎想挂断了,出于一种不知名的逃避心理。
他刚伸出手,便听电话那头有了动静。
声音像穿过老远的地方,如果不是亲耳听到,祁阳是不会相信陶陌能有这样温柔深情的语调。
“对不起。”他说,“祁阳,对不起。”
陶陌抓的其实很准。
祁阳这人,表面看着清淡寡言好说话,实际脾气拧的不比谁差。典型的吃软不吃硬,如果陶陌一开始是解释或者推诿,那估计话只开了个头,就要被无情挂断拉黑了。
偏偏,陶大总裁打的一手好感情牌,根本没有自己的总裁公众包袱,开口便是低姿态高诚意的道歉,赶在祁阳还在犹豫不决的当口里,成功抢占了一个缓和的余地,让祁阳的神色微微松动了一点。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补救的机会,让我弥补自己做下的过火的事情……但是祁阳,我说的话是真心诚意的,我喜欢你,我不会把这个当成一个错误。”
陶陌的声音透过话筒稳稳的传递了过来,咬字清晰坚定,语调温柔认真,撩的祁阳抿紧了唇,心头只是瞬间的泛出点点涟漪后,转眼便被理智的权衡给代替了。
在之前,他可以只考虑自己跟陶陌之间的事情。
现在,他必须有别的需要承担的东西。
祁阳的目光落在诊断书上,缓缓深呼吸后,干涩艰难的开口,“……陶陌。”
那厢还在诚恳道歉的陶陌立时答道:“我在。”
“我……”祁阳的声音噎在喉咙中,喉结几番滚动,都难以启齿。
“怎么了,祁阳?有事尽管和我说。”陶陌预感到不对劲,敏锐捕捉到这是一个能当做突破口的契机,顿时耐心无限的轻声哄他。
百分之七十的成功率和二十万手术费的白纸黑字交替出现在眼前,想到年复一年坐在轮椅上黯然神伤的祁明,祁阳的手指猛然攥紧。
哪怕有百分之五十让哥哥康复的希望,他也绝不会放弃。
“我可以当什么也没发生。”他咬着牙,“但是昨晚的事情……我要二十万损失费,只要你给了,就一笔勾销。”
电话那头陷入了沉默。
祁阳心里突了一下。二十万对于陶陌来说九牛一毛也算不上,难道是对方因为他借以要钱的行为感到不齿?
“二十万,我可以给,不是赔你昨晚的损失,而是作为你谈下洽谈会那笔单子的抽成奖金。”
“……”祁阳张了张嘴,嗓头酸涩,一时之间竟然发不出声音。
过夜的赔偿和谈生意的奖金,两个不同的名义,也代表了他或低或高的尊严。
陶陌,是在顾及他的脸面吗?
祁阳低低的笑了。
身为男人,被另一个男人压在身下做了这样耻辱的事情,他还有脸面可言?
“不。”他说,声音轻而坚决,“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请陶总带头遵守,二十万,是赔我的损失费。”
无声的僵持了一会,陶陌无奈点头。
“好,我答应你,十分钟后检查你的账户,明天按时来上班,没问题吧?”
“没问题。”祁阳目光清幽的道。
次日,陶陌在办公室心不在焉的翻着合同,踩着上班前两分钟,才等到了期盼已久的敲门声。
他压了压声音,尽量不显得那么迫不及待,“进来。”
仅仅只隔了一天,他却好像一年都不曾见到祁阳一样,隐隐的还有些近乡情更怯的感觉。
来人推门而入,身段依旧笔挺削瘦,曾在他身下柔韧有力的躯体都裹进了严实的衣服里,连锁骨都不让他窥探到,面上的神色不再缓和,神色寒冬般冷冽,漆黑眼珠透出清冷的薄光,抿紧的嘴唇绷着漂亮的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