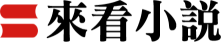飯後周南川送佟言回院子裡睡覺,佟言睡意全無,靜靜的在院子裡看他們幹活。
梁蓮花也在,低着頭默默地清理園子。
看到佟言她心裡唯有干着急,明明之前名聲那麼差,鄧紅梅對她也沒有什麼好臉色,跟周南川參加了個酒席,人人都說她好。
說她吃個飯一直都在幫周雪琪帶孩子,見到人也打招呼,客氣禮貌,不愧是大家閨秀。
西北的冬天,傍晚天色成了淺灰,淺灰中帶着幾片深灰色的雲,搭配在一起非常美得不像話。
佟言擡頭看着天空,看了許久,周南川注視着女人微微揚起的下巴,看她臃腫羽絨服之下的身軀,恨不得拿個東西給她墊着,生怕她閃了腰。
她看了好一陣,梁蓮花沒忍住,笑着問道,“嫂子,你在看什麼呢?”
佟言對這種灰調搭配的色彩完全沒有抵抗力,正愁找不到人分享,也沒顧及問的人是誰,“你看到了嗎,高級灰。”
周晨站在幾米遠之外的地方,“什麼灰?”
“高級灰。”
周晨沒看天,抓着半截就跑,在地上看了看,“哪有灰啊,最近沒到撒灰的時候。”
梁蓮花也沒搞懂佟言在說什麼,“嫂子,我怎麼聽不懂?”
“周南川,你看到了嗎,高級灰,你看看……”佟言拉着周南川讓他看。
周南川倒是過來了,但沒明白她口中的高級灰是什麼意思,“你看到了嗎?”
“沒有。”
佟言:……
她拿了手機拍了張天空的照片,但手機像素有限,拍不出那些詼諧的搭配色調,心裡多少有些失望。
“高級灰是什麼燒成的灰??”周晨不怕死的又問了一遍。
梁蓮花後知後覺才搞明白什麼意思,但她沒吱聲,裝作聽不懂的樣子,她就要讓佟言覺得她在這等於奇葩一個,她的話沒人聽得懂。
周南川也聽懂了,清了清嗓子,和佟言一起擡頭看她口中所謂的“高級灰”。
美術生抵抗不了高級灰的搭配,對這種色彩毫無抵抗力,他記得之前帶她買顏料的時候她買過一種,但後來他太忙,把這事忘了。
傍晚的天霧蒙蒙的,佟言在鐵皮屋裡等男人過來,周南川嗖的一下進來,立刻關上了窗戶。
一陣寒風湧進來,佟言打了個哆嗦。
“回家吧,過年前我們回家住。”
她捂着水杯起身,看了一眼男人身上的衣服,又看了一眼自己穿的,眼神下意識瞄到之前買給他的灰色外套。
那次周晨說他沒衣服穿,讓她給他買,但買了這麼久一直掛在那,沒見他穿。
上次她見到周雄慶,對方戴着名表,一看就是非常講究的人,鞋子穿得也都是好上千的輕奢品牌。
反觀周南川,穿的衣服單薄也有點舊,給人一種流浪漢的感覺,不像是結了婚的男人那般體面。
作爲當地的一個農場主,手裡好幾十個員工,他隨便得有點過了頭
正準備出門,佟言拉着他的手,他腳步一頓,人傻了,“怎麼?”
“周南川,你冷不冷啊?”
“不冷,我出汗了,一直在幹活。”
“那你累不累?”
“男人怕什麼累?”
“喝水。”她將自己的杯子遞過去。
周南川不明所以,真就喝了一口,一口氣喝沒了,拉着她的手,“走吧,早點回去早點吃。”
“我給你買的衣服爲什麼不穿?”終於說到了重點上。
周南川看了一眼,“白色的不耐髒。”
“不是白,是淺灰。”
“放着吧,我沒穿過那個顏色。”
“你試試,穿給我看。”
周南川擰着眉頭,有些不知道她在想什麼,“晚上穿這個?”
“我想看你穿這個顏色,行嗎?”
周南川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衣服,覺得身上不乾淨,“言言,我幹活一天,身上很臭,你想看的話等過年我穿給你看。”
“現在。”
佟言其實是有點怕他生氣的,但他沒生氣,乖乖的脫下了身上衣服,將灰色外套套在身上,買回來後他試都沒試過,這是他第一次穿在身上,這顏色給周南川的第一感覺便是不耐髒。
他這麼多年穿得最多的便是黑色,怎麼髒都看不出來,此刻這一身穿在身上,他不自在,走個路都怕蹭到。
周南川想開車,但天色很好,沒下雨外面風也不大,佟言便說走路一起回去。
周南川穿着一身淺灰色的羽絨服,和佟言並肩走在園子外面的小路上,這邊離周家村還有一段距離,白天有一些老式貨車經過,這會兒基本上只有幾輛電動車出行。
周南川這人有點封建,在外面不主動去牽女人的手,佟言也察覺到了這一點,不僅不牽手,和她的距離也有點遠。
她清了清嗓子,“周南川……”
“怎麼?”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
“沒有。”
那你怎麼不牽我的手,我們是夫妻啊。
話到嘴邊,她又不好意思說出來,頭頂是逐漸暗下來的天,男人的輪廓在微暗的視野中格外好看,不遠處一輛電動車過來,照亮了路,燈光打在男人的臉上,他身後是路旁的灌木和雜草。
頑皮的小伙子電動車騎得快,周南川將她往路邊一拉,護在身後,“川哥!”
路過的小伙子扔給周南川一根煙,他徒手接住卡在耳朵上。
佟言笑了一聲,他不知道她笑什麼,視線又回到了被陰暗籠罩着的環境中,她沒有這樣近距離仔細的觀察過這個男人,平日裡他不講究,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深色衣服籠罩着他,他不愛笑,對人平常,偶爾懟人,露出刻薄的樣子。
淺灰色的外套往他身上一套,他顯得比以往溫柔了許多,整個人線條也都柔和了,可這層羊皮並沒有掩蓋他骨子裡的痞氣,耳朵上夾着那一根煙,更是充滿了矛盾的美感。
男人跟着她笑,平日裡嚴肅的面容瞬間放鬆了下來,他覺得自己跟着笑不太妥當,欲將笑容收回去,但又覺得收回去過於刻意,被自己這種糾結再次逗笑了,抿了抿薄脣,“你笑什麼?”
“你笑什麼?”佟言反問。
周南川沒說話,舔了舔嘴皮子,忽然間很想親她。
他顧不上三七二十一,抓着她的小手往他衣服口袋裡放,“穿這麼多怎麼手還是冰的?”
“你這樣我不舒服。”
他太高了,她比他矮一截,小手被他抓着塞進他的口袋裡,這個姿勢有點費勁,她將手抽出來,又看了一眼男人耳朵上夾着的煙。
“周南川,你這樣好像個流氓。”
“瞧不起流氓?”
“不是瞧不起。”
她一看到周南川收起笑容,心裡就有點緊張,好像這男人隨時都會發火一樣。
“言言,沒人願意當流氓的。”
佟言低着頭,和他一起又走了幾步,“周南川,我沒有瞧不起流氓,只是我不想我孩子的爸爸被人說成是流氓。”
只有周南川知道,他在聽她說出這句話的時候下意識攥緊了拳頭,溫暖的灰色外套里,緊繃的情緒。
那年他高中畢業,無法翻身,求告無門,幾乎喪心病狂,他傾家蕩產買了一張去海城的車票想要跟佟經國同歸於盡,到了海城後卻連路都找不到。
海城真大,比整個臨西市大得多,大得他走了一天一夜也沒搞清楚自己身在何方。
那是他第一次出遠門,第一次見識到海城的繁華,原來一碗麵可以賣到二十塊錢的一碗高價,原來在海城根本沒有夜晚。
他第一晚沒有睡着,喪心病狂的走了一夜,他要找到一個叫佟經國的人。
次日清晨,晨曦在城市的某一端出現,天光大白,車水馬龍,人潮擁擠,他走在人羣中神色茫然。
他用了很多辦法,查到了佟經國的住處,城裡人看他的眼神,最開始是漠視的,淡然的,接着是詫異的,厭惡的。
他狼狽不堪,血氣方剛的年紀卻過上了流浪的生活,在這城市中活得像一團垃圾。
沒有人願意理他,見到他只會讓他滾,他嘗試着借陌生人的手機打電話,對方卻疾言厲色,“你再不滾我報警了!”
他道了歉,低着頭灰溜溜的離開了。
他在海城流浪數日,終於找到了佟經國的住處,他那種身份的人身邊一定有保鏢,他必須想一個萬無一失的辦法。
放火,燒了他全家,讓他生不如死。
他盯着那棟別墅,幾乎走火入魔,仇恨的種子在他心裡扎了根,開了花結了果。
直到佟言站在他面前,在他腳邊放了二十一塊錢然後進入那棟別墅,他這才認清楚——在他們這種人看來,他就是個要飯的。
他又呆了兩天,佟言每次見他都會給他錢,有一次小姑娘放學後叼着一根棒棒糖走在路上,見到他時理了理校服的裙子蹲在他面前。
“我媽說你們這種有手有腳出來討飯的都是騙子,你是騙子嗎?”
他蓬頭垢面,抵了抵腮幫子,就這麼看着她。
“哥哥,你有手有腳爲什麼不去找個工作?如果你真的是騙子,不要騙人了,我還有二十塊錢,都給你。”
他沒有同她說過一句話,單純覺得這個小姑娘長得挺好看,尤其是那雙眼睛,像是會說話。佟經國就這麼一個孫女,要是毀了他,佟家必會大亂。
佟經國怕周家翻身讓他無法上大學,死死的壓得他喘不過氣,如果他利用別的人去報復佟經國,那他跟佟經國又有什麼區別?
他去過幾個城市打拼,後來回到老家發展有了些起色,佟經國做夢也沒想到,一個大學也沒畢業的男人在數年後會對他造成如此大的威脅。
他中途去過海城,遠遠的看了她一眼,那時她穿着露肩膀的藍色小裙走在路上,美得不像話。
要是能娶到她這一輩子也值了。
有了這個念頭,便一發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