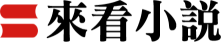縣醫院,周南川姍姍來遲,鄧紅梅大字兒不識一個,什麼手續都不會辦,忙進忙出打熱水,就像是要在醫院住下了似的。
男人穿着薄薄的黑色夾克,一條寬鬆牛仔褲,口罩遮住帶傷的臉,到一樓某窗口取了檢查報告。
眸色平淡,夾着一堆單子回到了病房。
“媽?”
病房裡沒人,去衛生間敲門傳來嘔吐聲,男人大手剛碰上去,門開了,佟言吐得站不穩,頭上包着紗布,幾點殷紅滲出來,她眼中氤氳着淚水,霧蒙蒙的。
他轉頭拿了紙巾遞給她,她吐得虛脫,用紙巾擦嘴。
噁心勁來得突然,她剛從被窩裡爬起來,身上沒穿外套,僅僅一件米色羊毛衫,微微彎腰還想吐,看上去格外單薄。
“喝水嗎?”
“謝謝,不用在這貓哭耗子。”
“不客氣,我也沒想幫你倒。”
男人戴着口罩,她卻能看到口罩下那張討厭的臉,男人要來扶她,她一手推過去,“滾!”
“佟言……”
鄧紅梅去食堂買吃的,發現食堂的東西很貴,爲了省錢跑到離醫院兩公里以外的地方去買,佟言不認得裝盒飯的包裝,周南川認得。
佟言紅着眼睛,沒有哭,氣氛有些尷尬,“吃點東西吧,人是鐵飯是鋼,你今天沒吃東西吧,啊?”
“我不吃。”
“你不吃孩子也要吃啊。”鄧紅梅這話並不全是關心孩子,但在佟言聽來是這樣。
手機打破了原本要持續下去的寧靜,佟言看了一眼手機,將屏幕對着自己,如視珍寶一般,眼睛更紅了。
“吃一口……”
佟言慌亂穿上鞋子,外套沒穿跑出去接電話了。
“佟言,佟言!這誰的電話?”
周南川眼睛一片漆黑,“你吃你的,外套我給她送去。”
佟言跑到走廊上,冰涼的溫度足夠讓她清醒些,兩個多月,他總算有消息了,按下接聽鍵,那頭聲音一如既往的好聽,帶着幾分暗啞。
“阿言。”
“混蛋……”
那頭笑了,“前段時間處理一些事沒辦法跟你聯繫,剛騰出手來,晚上我來接你……”
眼淚在眼眶裡打轉,佟言蹲下,“別來了。”
“還生氣?”
佟言不會生秦風的氣,就算表面裝得很生氣,內心卻早就原諒了他。
“阿言……別哭了,這次情況有點特殊,我見面了跟你解釋。”
佟言捂着嘴,不讓自己的哭聲被他聽到。
對面靠走廊那道門旁,周南川的筆直的身影遮住了光,眼淚在眼中凍結了幾秒,緩緩垂落,一下又一下。
她朝周南川搖頭,乞求的眼神求他。
“跟誰打電話?哭成這樣?”周南川眼中幾分譏諷,在她面前蹲下。
內心兵荒馬亂,她閉上眼睛,那頭警惕十足。
“阿言,誰的聲音?”
周南川過來搶,佟言捏着手機不松,跟着男人的力道起身要去搶過來,被男人堵在牆上。
動不了,一點也動不了,他一隻手就可以戰勝她兩隻手,她那點勁給他撓痒痒都不夠。
“求你了……”
秦風捏着黑色絲絨小盒,打開又關上,戒指發出耀眼的光彩,“阿言,你在哪?我現在來找你。”
“你不用來找她,她也用不着你來找。”
秦風輕笑,“你特麼誰啊?”
“她男人,周南川!”
手機被周南川掛斷,她想解釋,卻不知道從何解釋,“把衣服穿上,別着涼……”
她扇了他一巴掌,毫不留情,“我讓你滾。”
“滾哪裡去?”
佟言受不了了,想到秦風正在另一頭胡思亂想,她喘不上氣,“周南川,我現在回海城,我會說動我爺爺跟你離婚,這件事我會想辦法解決,嗚嗚嗚……我受不了了……”
“走可以,孩子留下。”
她腿一軟,呆在原地。
不過兩個來月滄海桑田,秦風出事,佟家履行和周家的約定將她嫁給周南川,她在新婚夜被周南川強要肚子裡有他的孩子。
她能夠感覺到肚子裡的孩子存在強烈,胃裡隱隱作嘔,。
秦風回來了,她等不了了,可是要怎麼辦。
“佟言。”
她擡手還要打,周南川緊緊攥着她的手,冷硬的臉龐對着她,面部的紋理清晰可見。
她發了瘋,一口咬在他手臂上。
都是他的錯,他一句話就可以回絕,可他偏偏不,他不鬆口爺爺就一定會履行這個約定,她成了過去的恩怨的犧牲品。
周南川這次沒任由她咬,大步拖着她進病房。
她咬着男人手臂被拖着,儼然像個精神病患者。
“這是幹什麼?”
“媽,你先出去!”
周南川的話在周家頗有力道,他跺跺腳就能翻天,鄧紅梅放下筷子眼底幾分但又,男人直接將門關上。
佟言用了很大的力氣,咬得牙齒酸了,嘴裡一股腥甜,乾嘔卻吐不出東西。
“佟經國爲了彌補周家的損失把你嫁給我,聽上去是不是我們周家占了便宜?”
他不慌不忙撩開衣袖,隨意抽了幾張紙巾黏在傷口處。
佟言並不心軟,都是他應得的。
那晚她哭成那樣,嘶吼得啞了嗓子,他也沒有放過她,他每次占有都讓她苦不堪言,接下來的幾天,她走路都疼。
她沒開口,周南川用紙巾洗乾淨傷口的血,“你爺爺佟經國就是個僞君子,若不是逼不得已,他這輩子都不會來找我。”
佟言面色蒼白,嘴脣也是白的,內側隱隱有血,但不是她的,“他只是想彌補當年犯的錯。”
“他不是想彌補,是有人想大作文章,他怕這件事被揪出來,心虛了。”
“你胡說。”
周南川微微眯眼,笑得意味深長,“你不知道你爺爺多無恥我能理解……”
佟言擡手要打他,男人死死鉗着她的手腕,“我爸媽在鄉下活了一輩子,沒什麼心眼,以爲人心都是肉長的,你爺爺那幾句話他們當真了,但我不傻,老東西狐狸尾巴早露出來了。”
“你敢罵我爺爺……”
“我罵你爺爺怎麼了?”
周南川強勢起來,禁錮她兩隻手,把她放倒在牀上,“讓你躺好就給我躺好。”
眼淚一滴,兩滴,接憧而至,“我爺爺只是爲了彌補。”
佟言不懂這些勾心鬥角,若是乖乖的嫁給他好好過日子,他會對她好,可她來了後沒給過他好臉,那副高高在上的優越感讓他無數次想將她踩在腳下。
結婚那晚上他就是故意的,他知道她會反抗,可他想讓她明白什麼叫尊重。
她腦袋裡沒這個概念,壓根兒沒正眼看得起他,覺得他是個流氓,牲口,土鱉。
他倒想裝聾作啞,就這麼過,可佟言現在非要跟他鬧。
是時候讓她知道佟家都是一幫怎樣的豺狼虎豹。
“你爸和潘年現在各自擔任要職,半斤八兩,明年的海城的提干,在你爸和潘年當中二選一……”
潘年爲了抓佟家的把柄,找人揪到了佟經國小辮子,佟經國也不是毫無防備,察覺到些許風吹草動便有了警覺,怕事情抖出來,也怕周家的後輩和潘年聯手拉佟家下水。
索性將佟家唯一的孫女塞出來平事,結成親家關係也就近了,誰敢在背後指指點點。
把她嫁過來不單單是爲了彌補周家,更是爲了掩蓋當年的醜事,佟經國雖然退休了,但他也想在功成身退的情況下必須保證佟家豪的前途不受影響。
“你現在回去潘年立刻就會來找我。”
這件事傳出去必將引起關注,佟家豪能不能提干是小事,整個佟家老底兒都可能被掀出來,到時候革職的革職,搞不好還會面臨官司。
佟言含着金鑰匙長大,很小的時候便過上了很優越的生活,佟經國退休前因職位的方便給整個佟家渡了金,逢年過節送禮拜訪的親朋好友從未斷過,現在爸爸佟家豪正值提乾的大好機會,佟經國怎麼能允許當年自己的一念之差拉兒子下水?
過去的那些歲月里之所以能那樣無憂無慮都要感謝老一輩的努力,只是此刻回想起來,竟覺得後背發冷。
“周南川,潘年是個不擇手段的卑鄙小人,他跟我爺爺就不合,現在我爸上位了他心懷不軌……”
她有些語無倫次,男人清理完手上的血,將袖子放下來。
“單是爲了彌補我敬他是個英雄,這是他結婚那天讓我簽的文件。”
佟言一目十行,很快看完,看到了上面雙方的簽字,撕得粉碎,“不可能。”
“他知道當年的事意味着什麼,但他依舊在我爺爺毫無防備的時候灌醉他,撕碎他的資料,在我爺爺告到村上去的時候裝無辜,否認真相,他進城後我爺爺被罵了一輩子,是他做賊心虛,可過去這麼多年,周家依舊被人在後面戳脊梁骨。”
佟言垂着頭,周南川挑起她的下巴,“現在提及不過幾句話便能概括,但這幾句話是我爺爺的一生,也是周家這幾十年裡作爲受害者的待遇。”
“心術不正,上樑不正下樑歪,牲口,混賬……這些話有人對你說過嗎?。”
她麻木看着他,男人冷笑,“你說佟經國哪來的臉讓我簽保密協議?”
“周南川……”她聲音沙啞。
“我知道算在你身上不合適,但你這麼侮辱我也不合適,過去的事我不計較,我也麻煩你認清現實。”
手機屏幕亮了好幾遍,雖是震動,在這寂靜的空間裡卻顯得刺耳。
周南川起身,將桌上的手機扔給她,“孩子我要,他若出了任何問題,我將整理好的資料發給潘年。”
佟言捂着心口急促的呼吸,男人腳步聲還沒徹底消失,她打掉桌上的飯盒,幾乎破了音,歇斯底里哭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