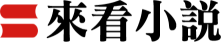西北某山村,佟言眼睛還沒睜開,胃中隱隱作嘔,她捂着嘴從牀上爬起來跑出門。
寒風嗖嗖往身上涌,她身上就穿了件棉質寬鬆睡衣,顧不上穿外套,瘋狂的嘔吐。
“嘔……咳咳……”
西北這地方哪有海城好?要什麼沒什麼,佟言伸手擦擦嘴,又是一陣噁心,嘔吐劇烈,眼淚直冒。
婆婆鄧紅梅從屋裡出來,遞給她紙巾。
她冷了對方一眼,“用不着你在這假惺惺的!”
鄧紅梅冷哼道,“狗咬呂洞賓。”
“你罵誰是狗?”
“罵誰誰知道。”
吵了兩個月,該罵的話罵完了,該打的架也都打得差不多了,彼此都有點疲憊了。
這不是近期第一次吐了,她心裡有些怕。
回到穿衣服出門,她塗了個口紅,脖子上纏了一根大圍巾擋風。
“去哪兒啊?”鄧紅梅有些不放心,多了一句嘴。
“我不是犯人,去哪兒用不着你管。”
她想去市里檢查身體,可這邊離市里要坐三個小時的長途客車,山路顛簸。
周家人知道她要去市里估計又會以爲她想跑,因此和她吵上一架。
平時無所謂,可今天身體不舒服,她沒力氣鬧了。
走出去沒多遠聽到鄧紅梅打電話,“出門了,不知道啊,今早吐了……”
“她不說,我哪兒知道因爲什麼?”
周家村的衛生院不大,外面橫着一張紅色橫幅,“和諧社會和爲貴,男女平等人爲本。”
在衛生院上班的人認識她,知道她是兩個月前周南川娶回來的大城市的老婆。
村里姓周的占多數,喜事就在村里辦的,能來的幾乎都來了,辦得熱鬧響亮。
給佟言看病的醫生明顯認識她,目光在她身上多停留了一陣,意味深長斂眉,沒主動跟她搭話,態度恢復平常。
佟言說了自己的症狀,對方遞給她一根驗孕棒,“去那邊廁所試試。”
廁所是水泥牆砌成的,髒亂差不足以形容,她看了一眼手裡的東西,還給醫生,“不可能。”
“讓你試你就試。”
研究了一番試完後,她目瞪口呆,醫生接過來看,“喲,這麼快就有了!”
“最末次月經是什麼時候?”
佟言腦袋一片空白。
她從來到這邊開始,天天顧着給周家人添堵了,她想把事情鬧大,鬧得周南川厭棄她,主動把她離了她就能順理成章的回家了,結果新婚第二天周南川覺得她煩,搬到園子裡去住了。
她氣不過,索性就跟婆婆鄧紅梅鬧,鬥了兩個來月,兩敗俱傷。
她以爲是長期壓抑導致生理期延遲。
可是想想,好像有將近兩月沒來了。
佟言照實說,周醫生笑着看她,“那恭喜你了,你公婆得高興壞了。”
這種事有人高興有人愁,頭頂的天,眼前的樹,村莊,田地,農舍——頃刻間成了灰色。
她跟這破地方沒緣分,之所以淪落至此,是因爲爺爺佟經國。
佟經國老早是這村裡的人,當年跟周老爺子周盡忠是好友,爲了爭取大學名額,佟經國灌醉了周盡忠,撕了他的資料,得到了名額上了大學。
佟經國進城後混得相當不錯,心裡有愧便想彌補周盡忠,所以便將自己親孫女佟言許給了周盡忠的孫子周南川。
這是佟言聽到的版本,可是後來佟言才發現,爺爺說了謊。
她千不願萬不願,卻不想家裡爲難,在爺爺的要求下硬着頭皮來了這裡。
二十歲的年紀,海城少年班畢業的美術生,來到這窮鄉僻壤的地方不是來採風的,是來嫁人的。
新婚夜那天,周南川喝多了,不顧她的反抗強行行了夫妻之事。
她沒想到會這麼快面對這種事,沒有半點準備。
被占有的時候她哭得幾乎使不上力氣,每一下都像刀子在割,用盡全力阻擋不了半分,剩下的絕望與疼痛,從一處到全身蔓延開來。
次日清晨,她拖着身子從牀上爬起來找男人拼命,周南川不理,當天就搬出去住了,躲她跟躲鬼一樣。
事情傳開了,全村人都罵她沒半點當老婆的樣子,是個母老虎。
周家爲了娶她如此大辦一場,全村都轟動了,可她倒好:結婚第一天就把男人往外面攆。
佟言在心裡爲自己辯解過,她不是母老虎,是周南川做得過分,那些人不知道周南川怎麼不顧她反對做出那種畜生事。
可從今天開始,她把母老虎的頭銜徹底悍在了頭頂上。
園子裡,周南川和本地的幾個農民商量蘋果產量,幾個女幫工摘蘋果,用剪刀將被塑料袋包住的蘋果沿着根部一點點剪下來。
佟言手裡拎着一把菜刀,赤紅着雙目,在衆目睽睽下一步步逼近周南川。
不知道是誰喊了一嗓子,“川哥,嫂子來了!”
周南川下意識往那邊看,佟言的刀扔過去,落在他腳邊,小身板下一秒朝他撲過去,擡手往他臉上一抓,動作之快,五道痕跡火辣辣的疼。
周南川反應過來抓着她胡亂動的手,女人的指甲掐進他的手背里,刮一下一層皮都沒了,他喉結滾動,忍住了想罵人的衝動。
一羣人跑來拉架,個個拽着她,見證她崩潰嘶吼的樣子。
被拉開後佟言被帶到園子裡的鐵皮屋裡。
爲了防潮,鐵皮屋是下面由四根鋼筋固定,鋼筋支起了整個小屋子,側邊一道木板梯。
窗戶半開着,下面堆着幾箱蘋果。
周南川在外面抽了一根煙,進來後板着一張臉,在她對面坐下。
他搬出去後開始兩人便沒有再見面了,氣候原因,他臉上的皮膚比夏天白了點,可底子在那,依舊比一般人黑一點。
男人開口說話的聲音有點干,“來幹什麼?”
他也注意到佟言比剛來的時候瘦了點,唯一不變的就是眼神。
她冷得眼睛鼻子都是紅的,明明很認真在看着他,可那眼神頗爲嫌棄,慘雜着幾分不得不的忍辱負重,就像在看一團垃圾,忍住不讓自己吐出來。
這種眼神讓人倒極了胃口。
“沒什麼事我讓人送你回去。”
“我要打胎。”
“什麼?”
佟言擡頭,語氣中夾雜着小火苗,“我說我要打胎。”
靜默了半餉,周南川站直了,“有了?”
也不知道觸碰到她哪根神經,她踮腳給了他一巴掌,男人抵了抵腮幫子。
“我要離婚,周南川,我要離婚!畜生……”
一邊說一邊哭,眼淚就跟絕了堤的大壩似的。
她喜歡秦風那樣的,笑起來時臉上有酒窩,給人感覺很乾淨清爽的,待她溫柔小心,處事老練沉穩,而不是周南川這樣,五大三粗黑得跟塊碳似的,說話又絕又狠,目中無人,從不給人留面子,還大學都沒念過。
園子裡幾個幫工在外面偷聽,個個面面相覷,佟言見周南川沒還手,又是一巴掌,“聽到沒有,帶我打胎,我要離婚!”
周南川被她打得臉上沒一處好,“你爺爺同意我沒問題。”
“他們不同意!”佟言急得跺腳,“我不想在這破地方,不想給你生孩子,你怎麼不去死?”
情急之下什麼惡毒的話都能說得出來。
周南川愣了一下,佟言拿起桌上的水杯朝他臉上潑。
水是燒熱的,潑在他臉上冒了一陣白煙,他擡手。
佟言嚇得捂着腦袋,以爲周南川要打她。
結果對方只是擡手抹了抹臉上的水。
他手上髒沒來得及洗手,臉上被抓得血淋淋的,熱水一淋冷風一吹,臉都麻了,髒東西都進了傷口裡,疼得想冒火。
在村里他是出了名的暴脾氣,十來歲的時候跟一羣混混在縣裡到處躥,惹事生非,是大人眼裡的刺兒頭,對於他的高中文憑,村里人都說是瞎貓碰上了死耗子。
男人轉頭就要出去,佟言又冷又怕,卻也是急了眼的,抓着他死活不讓走。
“帶我去打胎,答應了就讓你走……”
男人陰着臉將她的手扒開,她又抓上去,扒開,又抓上去,周南川惱火了,還想去扒,她將指甲鉗進他的肉里。
“嗤……鬆手!”
“不松!”
“我讓你鬆手!”
“帶我去打胎,跟我把手續辦了,我要回海城,你親自去跟我爺爺說,只要我能做到的你可以隨便提!”
周南川將她的手扒拉開,佟言沒有半點心軟,手指甲抓得更深。
男人一把將她推開,轉頭下板梯。
惹不起躲得起。
剛邁下兩階板梯,佟言紅着眼睛追出來,從他身後推了一把,推過去卻沒推到位置,從他胳膊滑過去,整個人往階梯下面摔。
“嫂子!”
周南川回頭順勢抱着她,兩人從板梯上滾下來,佟言穿得多沒什麼事,腦袋也被周南川護着,滾下樓梯人都懵了。
男人擰着眉頭,大臂磕在板梯上,颳得血肉模糊,臉上痕跡顯而易見。
“川哥!”
“嫂子你怎麼樣?夫妻之間有什麼不能好好商量,動手幹什麼……”
也不知道是冷的還是怕的,佟言嚇得發抖。
男人朝她走了一步。
捂着頭沒忍住叫了一聲,做好了被打的準備,心裡依舊打着算盤。
搞不好周南川打她一頓,她就能想辦法告他家暴,這樣爺爺也就沒話說了,總不能爲了彌補周家,真的把親孫女推入火坑。
周南川看她倔強又嫌棄的眼神,原本是沉着臉的,此刻卻冷笑了一聲,“打的時候不是很有脾氣,起來繼續啊。”
她站直了,“你以爲我不敢?信不信我咬死你……”
男人又是一聲冷笑,園子裡幹活怕熱,他一件黑色長袖,挽起了一截露出精壯的胳膊,朝她伸過去,“咬啊。”
她沒動,厭惡的眼神呼之欲出,下一秒被男人強勢摁着頭,腦袋撞在他胳膊上。
“啊!”
“咬啊,你來咬。你特麼今天咬不死我別想回去!”
衆人紛紛來拉架,園子裡亂成一團……